木兰无名
“名字里的沉默”——没有姓名记载,是救父故事中最多见的一类。
高高的祠堂建起来后,供奉的人物却没有姓名。这种反差,在表彰孝女的场合,并不少见。
唐代宝历年间,朝廷大肆冶银,在金谿(即金溪)也置了场。负责人长期努力也完不成指标,“岁久,银不足以充贡”,不但自己锒铛入狱身受折磨,而且倾家荡产也补不上亏空。他的两个女儿抱头痛哭,哀叹不是父亲不尽心,实在是资源和产能有限,国家要求的额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认为父亲大概是救不了了:“若罪不可赎,女生何为?”绝望中她们使出了最后一招——两个少女,活生生地跳进热腾腾的冶炼炉,尸骨无存。
绝招总算有用。对生者,父罪得脱,民害被除,因为刺史上报了此事,使朝廷收回成命,贡即停,后来者少受折磨;对后世,善政得以延续,“邑人世世赖之”,宋代在此置县,县名就叫“金谿”。元代本有郡守打算重启冶银计划,但念着金谿当地曾为此闹出人命惨剧,所以只能将此地的计划搁置。因此,元人刘杰写了《重建孝女祠记》并感叹,二女“其功大矣,祠之,于礼为宜”。
但相比肯定“非二女捐躯一死,其父之罪可释乎?后人之患可逃乎?”的大功绩,刘杰开篇应景点名夸赞的是王知县初上任即政平讼理并重建孝女祠(于县东之滓堆)的政绩,表明撰文刻石、长久保存的用意,接着便说“孝女二人,忘其姓氏”。这个“忘”字,意味深长。
不记姓名,无形中也给了众人更多想象的空间。宋代名将岳飞,相传有一幼女,其父被逮,女负银瓶投水死。人们为此女也修了祠堂,据元代杨维桢所记“祠在浙宪司之右”,他的《银瓶女》诗,笔法与刘杰记唐代二女事迹相似:
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
杭州人建张烈文侯祠供奉张宪,觉得张宪该娶岳飞的小女儿,便塑银瓶像以配之。清代的俞樾善考据,他对银瓶女的身世和下落做了彻头彻尾的考证,观点是其事应有,但把岳飞幼女和张宪“拉郎配”的民俗,在守礼的儒士心里过不去。俞樾的《曲园杂纂》中有一篇《银瓶征》,细细考辨了此事。
岳家有无此女?俞樾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一方面,《岳忠武行实》出自岳珂,应该可信,但其中所列出的岳飞的儿女们都有明确的名字或排行,“独无所谓银瓶者”。难怪人们心生疑惑:幼女殉孝也该算得上突出事迹了吧,但岳家平反后,为何没有表彰?“岂不经御旨追赠?”另一方面,俞樾又找到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关于岳飞庙中“并祀银瓶娘子”的记载,推断银瓶姑娘的身份,至迟在岳飞死后百年已经得到了承认。
然而,就算殉父之女确实存在,但结合宋、元方志可推断,“宋时已祀王女而女不名”,也就是说,此女死后,名字并未随事迹一道流传。她非但名字不载于史册,甚至还被后人安排上了不同的名字。前人修《汤阴县志》,作《岳氏家谱》,直接说岳飞的幼女叫作“孝娥”。俞樾相当不以为然:她的精神可称为孝,不代表她的名字就得这么叫。
当然,俞樾更不满意的,是后人把此女叫作“银瓶小姐”,因为这至为不典,恐怕玷污了岳飞幼女的清白名声。对此他认同赵翼的看法——“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比如宫婢称小姐、妓女称小姐。因此岳飞的女儿一定不能被叫成“小姐”。俞樾又依据宋代无论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载之这一点,推断“小姐”其实是从妓女的雅称“小籍”转来的,还曾因近人记载中的“银瓶小姐”,差点儿把为岳飞而死的女子认作岳飞家妓而非岳飞女儿,直到得知元明以前的记载中她都叫“银瓶娘子”,他才放下心来。
俞樾还列举了人们如何围绕“银瓶”做文章,展开对无名孝女的想象。有人说,岳飞夫人梦中抱银瓶而生女,女因此得名,正应了《易》的井卦,说明她出生时便有凶兆。又有人说银瓶是岳飞送给幼女的礼物,父亲下狱后,她曾设法搭救,无奈希望破灭,才抱着父亲送的银瓶投井,年仅十三。这些孤证,俞樾找寻来,丰富了故事的可能性,毕竟最初的记载只有岳飞死后其幼女抱银瓶投井自尽而已。
岳家幼女是否婚配?俞樾前面一番辨析和罗列,把故事的要点放在“幼女死孝”上,于是传闻不攻自破。岳家银瓶女还小,张宪则早已是岳飞爱将,二人“年齿悬殊,岂可以为配乎”?硬要“以数百年后,强为作合”,把未婚而死的孝女安排到将领张宪的身旁,不妥。
岳孝娥抑或张岳氏,银瓶娘子或是银瓶小姐……围绕这位勇于赴死的少女的身世与故事,前面俞樾考证中所引述的传记、方志、笔记与传闻,以及办得有声有色的祠堂,足以显示出古人评判孝女时的一些规律:从“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到“岂可以为配”,与其说关心她们的安危,不如说更在意她们的无私贡献和清白节操。孝女不能失名节,士大夫的标准一贯高,反观民间搞供奉、拉郎配、看热闹,让忠臣做了岳飞女婿,给小姑娘许个好人家,在以身殉国或殉父的悲剧中也要努力搞一搞“大团圆”,哪个更贴近事实?哪个更理想?她的生活该由谁来讲述?这些故事中的理想状态又是谁的理想?
按理说,本书的主角缇萦(汉)与木兰(相传为南北朝),早该出现在金谿二孝女(唐)与岳家银瓶女(宋)之前。之所以开篇数页仍未写到她俩,不仅因为她俩在后文中“戏份”更重,而且因为她们其实与所有救父者共命运。无论是因更广为人知而被浓墨重彩书写,还是影响仅及于一时一地;无论是年少赴死,还是下落不明,她们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绎过,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时也被遗漏了个性。
最初我关注的,是缇萦、木兰等人的救父谋略和冒险精神,但追问下去,发现故事里并不只有谋略和冒险,在这之外,她们背负着更多,同时也失去了更多:少数取得成功和荣耀,更多的是挣扎与内耗,无数失败与绝望都由她们自己承担。他人多强调局部,我更想看到整体。而当我试图看到她们整个人生、看清她们每个人时,名字的模糊与事迹的漫漶构成了重重障碍。前面细辨银瓶娘子(仍然不确定该怎样叫她)青史不留名乃至流俗乱编造的例子,正是名字“沉默”引发的乱象,同时也是面对关键历史信息缺失时如何“解谜”的一把钥匙,若善加解读,也许能比那些按照“孝道模板”组织材料撰写出来的模范故事,透露出更多的东西。
察觉到“空白”和“乱象”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追问——而只有把问题问对了、问清了,对每个时期都有的“救父”故事,才不会仅看作“孝女”主旋律的重复,而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故事细节和人物个性,看到更多故事里的她们。
岳武穆鼎鼎大名,其幼女“慷慨赴死”是非凡之举,但这样的名门之女,名字也早已“失传”。我因此猜测,如果是真“小姐”(妓女),更难得留名。果然,陈岩肖《庚溪诗话》中有一个宋代官员康执权“戏为一绝”的故事,他作诗是应了一位意图救父的妓女的请求,而这个妓女自然也没有留名。
这个故事展现了士大夫之间的默契,也留下了一首七绝。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永嘉有个姓山的官妓,某日她父亲山某不知何事被抓,“以事系县中,当坐罪”,山女士哭着求遍了与她往来的士大夫,其中康执权从前就因为山女士“颇慧丽”而常找她陪酒,这次便伸出援手,作诗一首,给她支招。山女士依言,第二天到县里投状说要代父受刑,状里还带上了康执权的诗。知县一看,“笑而释之”。
士大夫们的“戏”与“笑”,正好与山女士的“泣”与“乞”形成反差。举手之劳的诗,也确实举重若轻:
昔日缇萦亦如许,尽道生男不如女。
河阳满县皆春风,忍使梨花偏带雨。
这是将山女士的请求升华到与典故中缇萦救父一样的高度,也是一口气送了知县两顶“高帽”:春风化雨、崇尚教化的父母官,怜香惜玉、成人之美的君子。如此便艺术性地化解了山女士的麻烦。果然文人和官员才是记事中的主角。山女士的努力,只有被比附于孝女典故,依附于才子佳话,才有了被记下来的意义。至多,因为她的官妓身份,诗话中多描绘了一笔她的慧丽与柔弱,使她多了一些救父的筹码。
跟宋人帮着山女士说话的策略一般,元朝儒者的《银瓶女》,也要通过提及汉时的缇萦之名,来与宋代少女的孝相呼应:“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其实汉唐以降,几乎每个救父故事都会提到缇萦,如果有女扮男装情节,还会拉上木兰。在众多被遗忘的名字中,在大量模糊的面目里,缇萦之名被一再提及,拨动着主旋律。这既衬托出缇萦的典型性,又暗示着记事者的图省事与当事人的“沉默”。所谓图省事,就是把诸多事件定性为“救父”,围绕着行动者如何“孝”来组织材料、叙述过程和结果,有意无意使之契合“缇萦救父”等孝之典型,有无名字,细节如何,都无甚干系。千篇一律的劝孝范本,凭空略去了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以至于古老的故事变成了空壳,改个名字,可以一说再说。
缇萦无踪
缇萦无下落,木兰不知名,两位孝女的命运,像是形成某种“绝配”。前面说了“木兰”不知是姓是名,而淳于缇萦虽有名有姓,但如果不是自始便受关注的话,她救父之后如何,早已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缇萦,是个被史册记录下来的孝女,但在此之前、在文字之外,她不可能只是个孝女。同理,后来的救父者们,被缇萦等典型激励而踏上险路,又纷至沓来地来到文人墨客笔下,女入《列女传》,男入《孝义传》,纷纷被打上“孝女孝子”的印记。这其间,失落的又何止名字,还有性命(如果救不成)或去向(万一救成了)。他们极少全身而退,事败自然粉身碎骨,事成往往因书写者的“任务完成”而“下落不明”。他们的一生简直像流星划过,燃烧生命只为救父这一高光时刻。而书写者更关心的,当然只是这些能彰显礼教纲常的高光,在他们笔下,救父者仿佛只为完成特定任务而活,这种“中心聚焦”,反过来看,便是周边虚化。不信,你就去问:木兰(假如真有其人)真名叫什么?缇萦救父之后(如果还活着)过得好吗?除去被虚化、被省略的,唯有沉默。
历史上的救父者,功成身死者有之,功成身退者有之。提到后来去向的,大致分为两类:要么融入日常,要么脱离日常。功成身死恐怕是她们最激烈决绝也最感动史家的宿命——年轻而无辜的生命戛然而止,以此来最后回报生养者的恩情,书写者往往对此浓墨重彩大肆渲染。而救父的生还者,实现目标后“下落不明”,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救父者不惜一切代价,书写者也因此而无暇他顾,只关心救不救得成,不在乎救了后如何活下去,大家心照不宣地把人活成或写成了“孝”的符号。
木兰在历史上的下落,也并不明确。原版《木兰辞》结尾,只停留在她还乡和改妆。亲情、爱情双丰收的大团圆结局,其实是后人的戏剧性安排,甚至还有不能免俗的想象,说木兰因为不想进宫而选择自杀,极似小说家言,可谓极大地满足了好事者的猎奇心理。将真正的战士、将领所具有的特立独行、坚忍不拔与艰难求生,都消解在“总得嫁个人”的固定桥段里。与银瓶祠里的拉郎配,何其相似。此类桥段所反映的,恐怕是民间延续千年的刻板印象。好比孝子若得皇帝青眼,那定然飞黄腾达、光耀门楣;孝女若是被当权者看上,从了,无非一入宫门深似海,不从,就只好以死明志。至于后者的“善终”,不外乎回归女子的本分——风光大嫁,相夫教子,夫婿和儿子飞黄腾达、光耀门楣,就是标准的大团圆结局了。
放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没毛病。可奇怪的是,在有下落的孝女的生平中,我几乎没见过这样标准的大团圆结局。
处于故事中心的缇萦与木兰们,尚且如此沉默、带着谜团,分给其他相似境遇的“孝女”的新鲜笔墨,可能更少。她们各有各的姓名、家庭、境遇。在相似的目标与坚决意志之外,她们不同的行动轨迹、丰富的“救父”策略与曲折的命运走向,也值得我们用心观察。诸如“缇萦救父”和“木兰从军”之类的典型情节,如果不用近代以降的“英雌”式的个人成就标准去衡量,而放回历史语境中,很明显有一条关于“家”的脉络贯穿其中,交织着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等关系。在这些多维的关系中,救父故事往往被大篇幅削减。但其中的不少疑问,实在是不能不提。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少的回答。那么久的沉默,是否还要继续追问?
本章最后要说的这类沉默,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且相对独立于沉默者本人。
先看她们个人。救了人未必就是剧终,至少要把救人者的下落算上,事件才近乎完整,而前述救父事件几乎都不是什么大团圆结局。更何况,即便有下落甚至是好的下落,也不等于前面的痛苦挣扎就没发生过。就算偶尔有所谓的成功,也不能认为这便是以喜剧收场。笔者曾以为,选择救父者,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一条悲剧性的道路。能转危为安只是小概率事件。悲剧意味着救父的代价沉重。
毕竟她们曾拼尽全力向命运发起挑战,她们本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可能。
而这些更广阔的可能里必然包括更顺遂的人生。不必救父的女儿,会度过怎样的一生呢?从无惊无险、无忧无虑的角度看,是幸运;从未发挥潜能、未见更大世界的角度看,或许也有遗憾。如果可以,她们自己会怎样选?正如劝孝者笔下很少展现救父者的惊惧犹疑,而对贤妻良母的称颂中,也很少会提及她们是否另有抱负。或者说,书写者替她们选了。白居易的两篇诗文,正好对应于此:命运的不同走向,呼应沉默的多个层次。
一是《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开篇写明,“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河南元府君讳宽夫人荥阳县太君郑氏,年六十,寝疾殁于万年县靖安里私第”。此文是白居易为友人元稹之母而作,他认认真真罗列了一堆死者生平各种贤良淑德,还提供了一组神奇的对比:
昔漆室、缇萦之徒,烈女也,及为妇,则无闻。伯宗、梁鸿之妻,哲妇也,及为母,则无闻。文伯、孟氏之亲,贤母也,为女、为妇时,亦无闻。
相比之下,“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这是和李翱夸高妹妹相似的写法。白居易在结尾也与李翱一样,升华到立楷模、美风俗的儒家教化目标:自己“与夫人幼子稹为执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孤慕,哀动他人,托为撰述,书于墓石,斯古孝子显父母之志也。呜呼!斯文之作,岂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闻夫人之风,过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嚣母慈,不逊之女顺”。死者已矣,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美名的传播也是她们生命的延续,是对她们毕生努力的肯定。
对活着的人呢?会讲道理又会享乐的大诗人白居易,目光看向自家小闺女时,又是寻常的老父亲心理:
吾雏字阿罗,阿罗才七龄。嗟吾不才子,怜尔无弟兄。
抚养虽骄騃,性识颇聪明。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
我齿今欲堕,汝齿昨始生。我头发尽落,汝顶髻初成。
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婴。缅想古人心,慈爱亦不轻。
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将来事未可知,眼前人正可爱,将心比心,“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女儿懂事,父辈慈爱,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才会懂得回馈爱吧。慈父白居易又说道,“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在老父亲这一边,诗成这一刻,七岁女孩白阿罗的可爱之处无非“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不必承担舍生取义之美名,毫无疑问也是被小心呵护的。而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和拼命保护别人的人,哪个更“求仁得仁”呢?
再看救父群体。从故事中元素的悲喜属性来看,缇萦和木兰顾不得问、史家和信徒不敢问的,如今我都想试着问一问。
首先,救父行动中的主角,各有几分信心?成功范例如缇萦,通过上书文帝获得皇帝垂怜,肉刑弊政得以改革,孝女故事被史书记了一笔。但这一连串事件中,小姑娘能决定的,也许只有出不出场。至于上书后皇帝看不看,皇帝看后感不感动,感动之后行不行动,行动之后谁响应等,都不是她能决定的。缇萦在“救父”中是主角,“刑制改革”中,她全家都只是“小水花”。后来的那些救父者,也一样没有万全把握。无辜少女少男的眼泪、乞求和性命,无非是强调以人伦亲情而换得一个“法外开恩”的机会。但开不开恩,决定权在皇帝或官员手里。而影响他们决策的因素,恐怕不只是孝女孝子的诚意或柔情。皇帝为何会法外开恩?是在什么局势下这样做的?救父成功是“托了什么福”?失败是否才是常态?围绕这些问题,其实掌权者有多重视“孝”的砝码,有多愿意为此而倾斜“法”的天平,才是决定一人、一家悲喜的关键。这些,讲述救父佳话、称颂孝女孝子的人,多半不会说。
其次,法律事是专业事,判决的得出,离不开“治人”,也少不了“治法”,试问遭了难、要人救的父,究竟犯了什么罪?是有心还是无意?是有罪还是有冤?该不该宽宥?这些也是评析救父故事的意义时,不可不问的又一类关键问题。讲故事的古人几乎“一边倒”地劝孝,要么给被救者找些值得同情的理由,要么直接一笔带过其如何犯事、因何获罪,比如现代扩写缇萦救父故事的名家,一定要把淳于意写成耿直善良遭人陷害,背后的原因值得细究。又如盐贩之女在古人笔下被说成令士大夫当反省自愧的坚守“信”的榜样,可如果我们记得“律令乃天下之大信”的话,她父亲长年侵吞国家利益来养家糊口,明显是故犯和累犯,那么官员应孝女一人的请求,豁免的是侵吞国有资产罪,这是否是对国家律法的“信”的违背呢?
正如前文所说应当探究救父者、被救者及局内人的思想与处境,跟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如何维护“孝”而“法外开恩”,同样耐人寻味。倘若被救者的故意犯罪不仅停留在贪图钱财层面,还意图谋害人命,甚至已经要了人命,加害者的子女要求情、代父受刑,被害“苦主”一方岂无子女?岂能甘心?于理于法说不过去的“不可救”之罪,偏有人自发或是被迫地求情、求救。这种异态,也同样是诸多救父故事的组成部分,更构成了法制天平的干扰因素。试想同类罪犯中,有人因幼女或幼子来求情而得到减免,有人却只能毫无商量地受罚,“孝”是何等强大的“灵符”;而当犯法者本人不悔改,因子女求情而获益后还敢再犯,即便作出决定的是皇帝,这“灵符”又将如何反噬决策者?古人倒可能被“孝感动天”的光芒迷了眼,封了口,如今却不然,无论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还是从“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理想角度,值得救的和不值得救的,还是得分一分。“如何救”与“因何救”,都不能不问。
一句话,她们愿意拼命是一回事,拼了命有没有用,是另一回事。
“请以种种真实之名呼唤我/我才能同时听见我所有的哭泣与欢笑/我才能看到我的喜悦与痛苦是一体。”(一行禅师)倘若那么多来路和名字被抹去、去路被略去、苦处被略去的救父者,她们的处境能被我们更多地看到,便真正能在历史现场中笑中带泪地鲜活起来了。
选择也好,处境也罢,都可以问。通过不断追问,真正看到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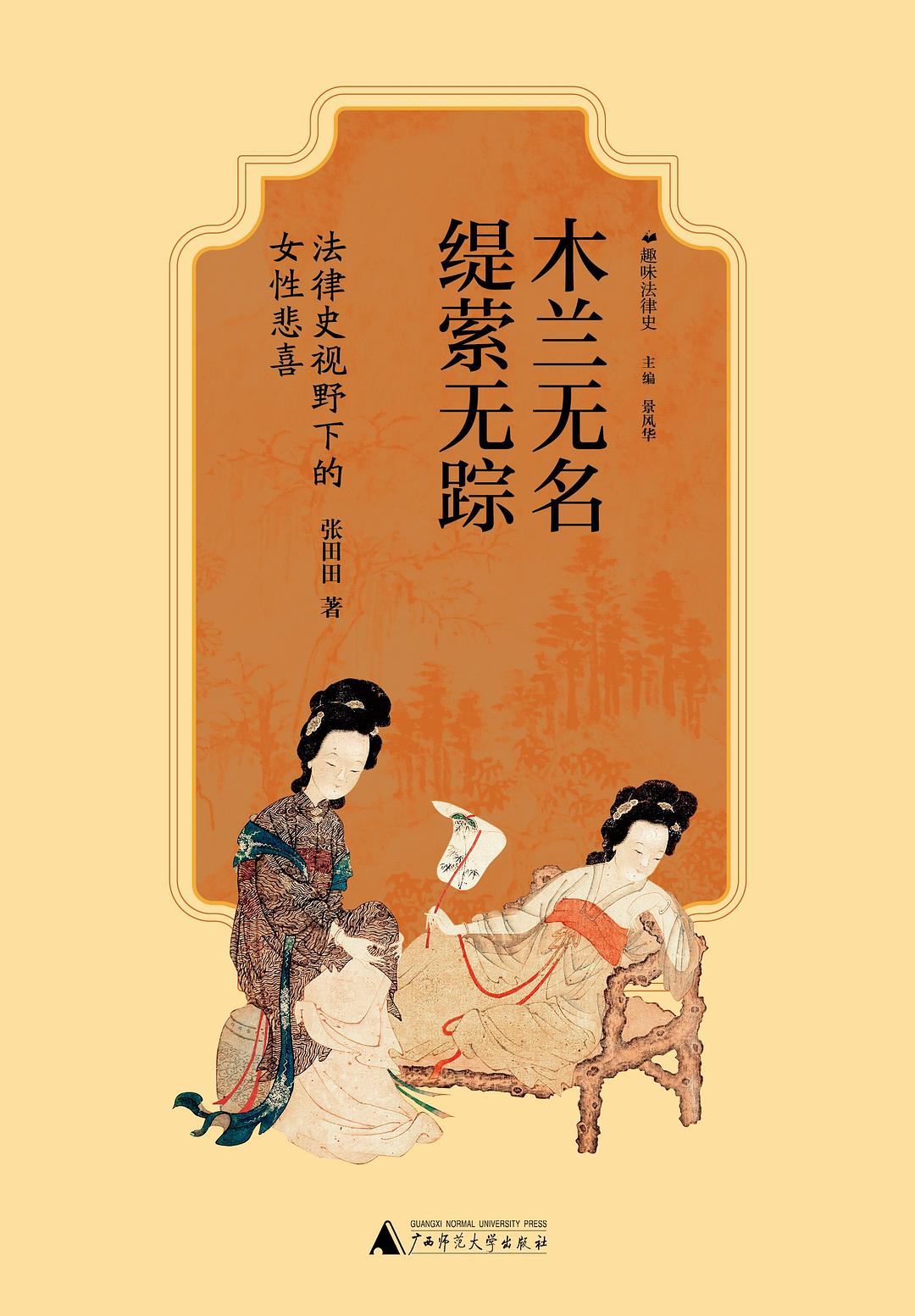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张田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