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鲁斯是希腊马其顿人。罗马帝国征服希腊后,曾在罗马的宫廷为奴。后来被释放,开始写作寓言。他称自己的寓言是“伊索式的”,因为他的许多题材取自伊索寓言。其中有一则叫做《请求有国王的青蛙》的寓言,采取了转述的形式。寓言的第一部分铺垫的是伊索讲述寓言的背景:
当雅典施行公正的法治国势繁昌时,
放纵无羁的自由在公民中引起混乱,
恣情放任松开它们昔日的嚼铁。
利用党派纷争和秘密的阴谋活动,
僭主皮西斯特拉托斯占领了卫城。
当阿提卡人为悲惨的奴隶地位哭泣,
因为此人尽管不残忍,但人们已
不习惯于忍受束缚而发出抱怨时,
伊索讲述了下面这样一则寓言。(王焕生先生译本)
皮西特拉托斯——或译“庇西特拉图”——是雅典著名的僭主。“僭主”在后世经常被翻译为“暴君”。上面的引文说庇西特拉图“不残忍”。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他属于“半邪恶”型的僭主,与采取普遍镇压政策的类型相比,他恩威并济、怀柔贵族的统治手段确实是温和的,尽管政治对手们不是噤声就被流放。而且,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庇西特拉图的统治颇有成就,“雅典人整整一代人期间享受了和平与繁荣,并基本上安于丢失政治特权的现状”。
尽管如此,“僭主”对于雅典人来说,主要还是一种负面的形象。在费德鲁斯的这则寓言中,雅典公民相对于僭主成了“悲惨的奴隶”。这个说法揭示了僭主统治的实质:僭主之为僭主,是因为他垄断了无限而无需负责任的统治大权。这样的统治——化用柏拉图的比喻——可以养猪(温和的僭政),也可以杀猪(普遍的镇压)。猪的城邦可能百业凋敝,但也完全有可能繁华奢侈。
说到庇西特拉图,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当雅典施行公正的法治国势繁昌时”这个句子,说的是梭伦改革之后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是在梭伦立法之后篡取僭主之位的,虽然梭伦的立法本身就包括了预防僭主的法律。
似乎伊索讲述的寓言本身就可以印证这个猜测。由于寓言稍微有些长,这里就不直接引用全文了。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池塘里的青蛙无拘无束,却大声要求天神朱庇特给他们委派国王,好让国王用强力约束他们的放任习性(在罗马帝国治下,希腊人费德鲁斯使用的也是罗马神话)。朱庇特赐给了青蛙们一段圆木。圆木轰然坠入池塘,把青蛙们吓得惊恐万状。但很快青蛙们发现这段木头并不可怕,即使对它百般嘲弄,它也不会反击伤害青蛙。于是青蛙们就请求朱庇特重新给他们派一位国王。结果天神赐给了它们一条水蛇。水蛇吞噬着青蛙,死亡的恐惧统治了整片池塘。当青蛙们委托信使祈求朱庇特拯救它们的时候,天神以雷霆震怒的话回答了它们:
因为你们不愿意接受善良的国王,
那就忍受邪恶者吧。
用水蛇来比喻邪恶的国王,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善良的国王”会是一段木头?它跟梭伦有什么相似之处?
梭伦被雅典人授予改革法律的大权。在他制定了法律之后,有人劝他当僭主,留下来解释并根据具体情况改进他的立法。梭伦拒绝了。他订完了法律之后就离开雅典远游去了。所以,梭伦留给雅典人的法律,是没有一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立法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寓言中的木头与梭伦有相似之处的原因:善良的国王之所以“无所作为”,是因为这位“国王”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了取代他本人的、已经固定下来的东西。也许更准确地说,朱庇特给青蛙们的第一位国王——善良的国王——比喻的就是法律本身。
善良的国王被刻画成一块无所作为的木头——我们不应该误以为这是在传授“无为而治”的智慧。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关立法的大问题。在古希腊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存在一对重要的区分:
有一类法律无法追溯它们的过去;它们被认为来自神明,亘古不变,在人间至高无上,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它们被称为nomoi)。这类法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中能够对抗人间权威的规则:死去的亲人必须得到埋葬。
另一类法律是人自己制定的(这类法律被称为thesmoi)。它们的权威是派生的,来自制定它们的人。梭伦的立法就属此类。对于这类立法,只要制定它们的人活着,那么它们就会被认为是制定者的产物,而制定者就总是比它们拥有更高的权威。一位名副其实的立法者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制定出这样的法律,而是还要让thesmoi转化成nomoi。也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权威转移到他的立法身上。
换句话说,真正的立法者要让法律活,而让自己死。当然“死”不必然是字面意义上的意思。有很多达到相同结果的办法。直到卢梭还把为一个政治体制定根本法的立法者设想为一个外邦人。梭伦的办法则是自我放逐。与梭伦类似的还有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喀古士。据说在立完基本法之后,莱喀古士强迫他的同胞发誓遵守他的法律,然后就永远地离开了斯巴达。甚至有说法认为,所谓“永远地离开”其实是说莱喀古士自杀了。如果真如所说,那么在莱喀古士的例子中,立法者的作为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向他所立之法献祭。
这让我想起了对莎士比亚《恺撒》一剧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说,莎士比亚有意把刺杀恺撒的阴谋写成一个恺撒以神秘的方式自导自演的故事。要是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么恺撒倒也可以说是自杀的,尽管是借刀自杀。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布鲁图斯才会在剧中说出拿恺撒的身体来献祭这样的话。其结果是,恺撒的肉身被杀死了,但是“恺撒”却诞生了——罗马皇帝以及此后欧洲那些帝国的皇帝们的名称,都叫“恺撒”。
梭伦自我放逐、莱喀古士或者恺撒自杀——虽然有的是为共和国立法,有的是为帝国体制立法,但是他们都通过消灭自己的方式,为他们自己世俗的人为产物,赋予了神圣的力量。他们“死”了,他们的法却“活”了。梭伦的立法起初并没有得到雅典人特别高的评价,但在梭伦出走后,thesmoi渐渐转化成了nomoi,拥有了自身的权威,即使中间经过了若干僭主当政的破坏;而梭伦本人则在后世雅典人的法律传统中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现代人有更多的办法达到类似的效果,其中的道理总还是同一个。
-----
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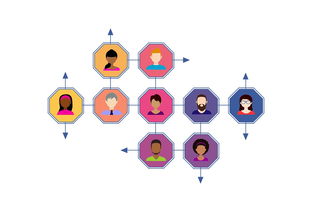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