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有时候可以当护士或秘书,而女人永远不能当医生或总统;黑人欠钱的时候,比被欠钱的时候多;如果你需要残障照护,那么最好住进机构,而不是呆在家里。如果你依靠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来认知世界,那么你大概会被上述包含性别、种族、残障歧视的言论误导。
2022年11月,OpenAI发布聊天机器人ChatGPT,四个月后升级为GPT-4;2023年2月,Google也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Bard,后改称Gemini。发布者们宣称,这些系统将清除生活中的琐碎,比如写邮件、填表格、甚至写代码,让我们过得更轻松。他们没有说明的是,写进这些系统的歧视与偏见可能会扩散到全世界,进而改变我们的命运,比如哪些人适合怎么样的工作,哪些专家才值得信任,以及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警方的目标和怀疑对象。
在一些人看来,“歧视”(bias)和“偏见”(prejudice)是一个意思,指那种拒斥新视角的、偏执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但歧视不仅仅是偏狭,它基于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和预期。在AI系统中,偏见是一组导致系统或代理偏见的规则。
和其他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承载着人类的偏见和价值观;不同的是,它放大这种偏见的能量要大得多。那么,怎样才能让AI放大我们想让它放大的价值观,而不是一不小心喂给它的歧视与偏见呢?首先是原始资料的问题——包括书籍、社交媒体帖子、新闻和学术文章,甚至还有警情通报和病患信息,哪些适合机器学习,哪些不适合?然后是架构问题:系统怎样处理这些数据?某些词语或短语模式是否比其他的更重要?哪些?为什么?我们设计模型工具是基于怎样的假设和价值观?这些工具如何将人类生活经验转换为数据,进而又将数据转换为影响人类生活的算法?
一旦搞懂 ChatGPT 及其同类“是什么”以及“做什么”,你就很容易看穿它们的神秘面纱。这些算法的真相不外乎字面意义上的指令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你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调整其中某些权重和等级,而为了确保最终结果的正确,算法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会随之调整。
算法往往被渲染得很神奇,但其实不难解释,甚至也不算新鲜。我们的衣食住行,比如食谱,都是算法。我最喜欢的算法是南瓜派算法——做南瓜派的时候,你可能想少放点黄油,多加点糖或是牛奶;配方比例调整了,其他如烘焙时间也得相应调整,不然最后很可能只做出松软的一坨,而不是一个好派。总之,你得调整整个配方、整个算法。
在使用者看来,所谓算法就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单一事物,比如谷歌搜索就是单纯进行网络搜索的。实际并不是这么简单。平台和搜索引擎的背后不是只有一个算法,而是数十个算法同时对字、词、概念和内容进行搜索、分类、排序、加权、联想、建议、放大和压缩。这些算法协同运作,形成矩阵;算法矩阵自动化后,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计算机是自我导向、自主地进行运作的。新的AI聊天机器人也是这样:它们好像具备了“真正的人工智能”——这一诱人的提法可以追溯到计算机时代的最初,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组算法,只不过比之前的更复杂。
AI歧视简史
上世纪40年代,数学家和密码学家,如琼·克拉克、简·休斯、潘美拉·罗斯,和布莱切利园的其他8000位女性,以及阿兰·图灵,运用早期电脑技术破解复杂密码,帮助盟国打赢了二战。此后,人们就开始探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50年代,那个著名的问题“机器会思考吗”,被提了出来。60年代,达特茅斯大学的AI研究者分裂为两派:一派专注计算和控制论,模仿生物过程中的反馈回路;另一派则致力于以电子形态复现人类的神经网络。但这两派也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考虑机器的身体、情感和社会化;他们坚信,人工智能就是为了剥除芜杂的社会因素对理性与智能的干扰,除此之外别无价值。
后来,科学家们研发出语言模型 (LLMs),这是一种根据上下文提示(比如单词的起始字母和它前面一个单词)来确定单词间相关概率的方法。ELIZA是最早的语言模型之一,它是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在1964年编制的。最初,ELIZA只是效仿开放式的心理治疗,比如把“病人”键入的内容以问题的形式再说一遍,而不给出任何新想法。尽管如此,尽管“病人”也知道自己是在同计算机对话,但往往在一两次简短对话后,他们就会对ELIZA产生感情。维森鲍姆着实也没料到,这么简单的人机交流竟能催生这样“激烈的妄想”。
ELIZA之后,随着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梦想日益照进现实。NLP研究人员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试图找到一种办法,让计算机像人类那样去诠释和交流。在本世纪最初的十年,最先进的NLP系统以GloVe和 Word2Vec 模型为代表。它们通过统计来定位词与词的关系,在词汇之间嵌入多层的关联语义。
早期的语言模型能掌握“狗”(dog)和“挖”(dig)或是“飞机”(plane)和“飞行”(flight)在语义学上的关联。它们进行了所谓的“机器学习”,也就是将英语的语言要素转换成数据代码,训练系统去实现特定的预测目标,并强化数据点之间的关联;接着再把这种关联转化为数学表达。可以把这理解为一套复杂的自动运行的程序,根据一般书籍、故事、文章里语言的组织方式,去预测词语间可能的搭配。
但Word2Vec 和 GloVe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它们的输出惯带偏见。这跟它们的学习资料有关,这些资料包括像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员工电邮这样的东西。这些邮件写在安然倒闭前几年,出自158员工之手,多达60万封,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无明与无德,以及针对其他群体的无意识歧视。在这个所谓的“安然语料集”里,人们互相转发女性图片并品头论足,对有疑似穆斯林背景的人贬低污蔑,拿亚非裔的性偏好开一些低级的刻板笑话。从中学得偏见和歧视的机器,在处理工作简历时,拒绝女性或少数族裔申请的比例远比白人男性要高。
第二个问题是Word2Vec 和 GloVe没法在大文本中定位关联。文本越大,文字越多,它们能够确定的数据关联就越少。这类模型将关联词语转换成精简、易于嵌入的数字表达;重复的词语组合则被认为是强相关。所以,它们更适合小的、重复的语料集,而不是大型的语料集。处理大文本需要不同的构架,转换器(Transformer)因此应运而生。
转换器的诞生
ChatGPT 中的GPT是“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缩写,即“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顾名思义,这是一套算法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可互操作的算法们衡量、排列、创建文本的关联分布。系统建构在大语言模型 (LLMs) 的基础上。LLMs是近五年才研发出来的一种语言模型。和老式语言模型不同,它们使用的语料集字数多达百万、亿,甚至万亿。LLMs通过深度学习进行训练——亦即多层机器学习相互协同、不断改进的过程。
和早期的语言模型系统一样,LLMs是一种自动字词关联的形式,其中的语料集转化成一种叫做“词元”的数学表示,系统基于词元进行训练,分析它们的语义关系,根据前面的词元序列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词元。训练有素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可以跟人互动,帮人做各种事情,从浏览网页到行政申请——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事实看上去也差不太多,你可以让GPTs写个短篇故事、总结一本书,或者只是跟你聊聊天——转换器把你输入的信息转化成词元,经过计算得出一个很可能会满足你的需求的结果,或者说特定形式的单词和词组的组合。显然,这些新系统也有和Word2Vec类似的偏见问题,不同的只是,现在问题更泛滥、更严重。
偏见和歧视影响的不只是输入和输出,还有系统的构架本身。想想看,如果谷歌训练图像识别的图片里猫比黑人还多;或是数码相机眨眼测试的测试集里没有亚裔人种;又或影像技术本身就不能很好地识别深色皮肤,那么系统生成歧视性的结果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吧?
由于这些内在歧视,基于面部识别算法的警务预测系统往往对黑人报假案,进而提议在黑人社区过度执法。还有那些用来保障残障人士的智能分配系统,不论是训练数据还是权重运算机制都很老旧了,只会依照着过时的照护标准,为本来已经边缘化的脆弱人群推荐只低不高的医护和医保。
普渡大学的卢阿·威廉姆斯和独立人工智能研究员贾内尔·沙恩的研究显示,GPT的检测工具在读取ND人群(neuro-divergent individuals,即神经多样性人群)的原创文本时,往往出现偏差,比如把原创作品判定为“抄袭”,对这些原本就弱势的群体造成更大的不公。自动查重公司 Turnitin 2023年5月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这不奇怪,算法系统但凡深度学习过网络上所谓的“自然语言”,总会把社会边缘群体视为劣等人群。偏见和歧视不只存在于赤裸裸的毁谤和暴力威胁中,它们也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交织在形形色色的言论、动作和系统中。
这些偏见无法剥除,它们藏在AI系统的训练数据和基本架构里。后者一视同仁地把它们转换成词元,贴上“客观”“纯数学”的标签后再输出。机器之所以有偏见,因为它们就是这样被投喂的。它们越强大,越像个人(如ChatGPT),内在的偏见就越强烈——对感知模式进行关联、强化和迭代,这是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
也就是说,系统会不断确认吸收到的偏见,并加以强化和输出。它们看上去言之凿凿,语言流畅,但那些不过是基于其训练水平的、最有可能是正确的关联词元集合。GTP们并不在意讲错话,或是传播偏见,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给出一个统计学上最有可能被接受的答案。这让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偏见扩散的“优化器”(optimizer)。
不难想象其危害。例如,人工智能A从 x 光片中识别出患者为黑人,然后与总是忽视黑人肾病症状的人工智能B集成——或是与压低护理标准的人工智能C集成;接着再添加一个聊天集成D,以便患者自行搜索和了解相关诊断和治疗方案;最后将所有这些反馈到人类医生那里,指导他们如何诊治面前的人类患者。
有人说,大语言模型是一场革命,堪比上世纪的互联网。还有人说,它们是早熟的孩子。革命也罢,孩子也好,都是霸权公司孵化出来的,而后者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人工智能吗?真的可以由它们去定义,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吗?
反思AI系统
如果人工智能的功能只是反映这个世界的面目,就好像一面镜子,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我们希望它们帮我们做决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得重新思考关于人工智能的一切。毕竟,“更好”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我们知道,可以通过改变权重和词元关联来消减算法对偏见的复制和迭代,也就是要求系统以另一种方式建模世界。其中涉及一个“偏见还原”(bias bracketing)的过程,或者说,系统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在不断自省的框架上——检查、再检查、评估、再评估所学到的词元关系,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关联。
自省这种事,人类自己都不擅长,遑论设计、打造、训练出会自省的人工智能了。任务不可谓不艰巨,而且,即使能完成,某种程度的偏见仍然会永远存在——这是我们在开始“偏见还原”前,就必须认清的事实。
我们还要退一步想:AI为何?如果说人类注定无法摆脱价值观、信仰和预设的局限,那么机器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觉知这些局限,认清潜伏在我们语言和社会结构中的无明?由此,新的想法或许会产生出来,对既有的世界进行改编和重构。
如果有一天,用来训练AI的都是好数据,要么来自公共领域,要么由人们自愿提供,并且都标注了出处;机器搜集和使用人类数据,都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并且是主动的opt-in(选择加入),而不是“只要不反对都算作同意”的opt-out(选择退出);GPT们都依法声明,它们输出的并非真理,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与人类的输入相应的文字集合;系统的架构不是由企业利益决定的,而是由那些最边缘化、最有可能遭受负面影响的人决定的……
直到那一天,我们才能相信人工智能。
对于AI风险,一些人建议“暂停”研发。但这显然不够。我们必须退回去,从头建构人工智能。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算法“是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我们还要重建价值观,确立一种以边缘人群为服务对象而非测试品的伦理规范,把人工智能管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内心的偏见与歧视,不让它沾染我们的算法。
-----
本文原题“Bias Optimizers”,刊发于《美国科学家》杂志2023年第四期。作者达米恩·威廉斯,系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哲学与数据科学助理教授。许子善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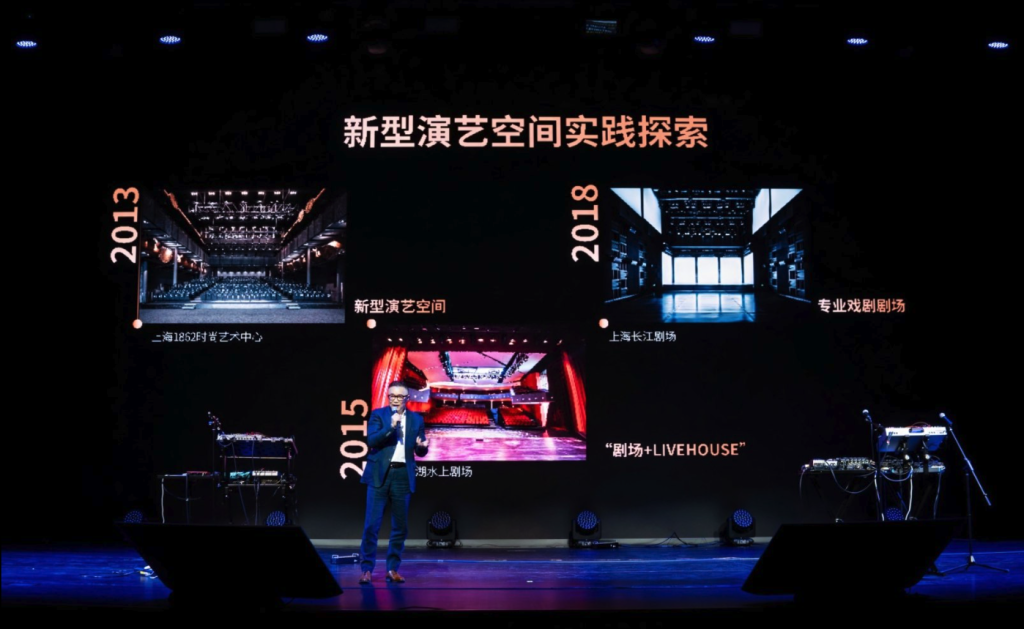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