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封面上那尊伏见稻荷神社的狐狸买下这本名为《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的小书时,以为书是关于日本狐狸文化的,而读完发现,实际上内山节这本书是追问、反思日本现代性的读本,尽管它的切口是那只灵动、鬼魅的狐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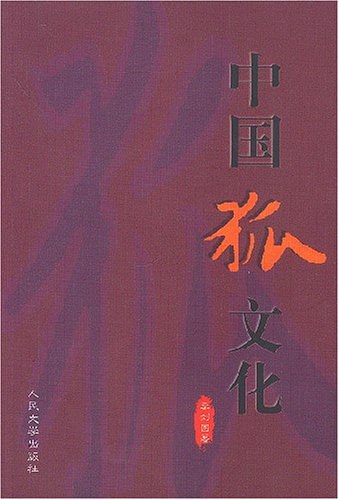
同处东亚文化圈,中国人对狐狸是不陌生的。无论是《封神演义》中女娲派遣的狐妖,或者是太史公笔下大泽乡如鬼魅般的狐狸叫,文学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李建国所著的《中国狐文化》一书系统地阐释了这种动物与我国文化的紧密联系,这种相遇、交织及其生发的复杂性,印证了作者在序言中说的——“狐精是中国文化的独创”,这一独特产物从古代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东邻诸国”,这其中当然包括日本。
前些年,手游《阴阳师》红极一时,在这个独特的职业细分领域里,最知名的就是活跃于平安时期的安倍晴明。实际上历史上的晴明通过观测天象、研修阴阳学为彼时的日本朝廷提供法理(天理)上的支持,类似于我国古代的钦天监。然而在民间,这位阴阳师则是无所不能的化身,他捉妖驱鬼,甚至偷天换日,为了让他的传奇获得一种确证,他的母亲被“安排”成一只狐狸,进而让民众相信晴明大人的非凡才华来源于这种多疑、神秘的生灵。

日本的狐狸传说起自于乡间,凡是村里人难以解释的怪事,基本上都是狐狸干的,比如家里的粮食被偷了,刚钓上的鱼不见……在八百万神行走的日本列岛上,狐狸总是妖力强大的代表。最近动画《夏目友人帐》开始播放第七季,影片中始终陪伴、守护主人公夏目贵志的是大妖“猫咪老师”,它的真实形态就是一种巨大的狐狸状妖精。与我们熟悉大部分日本当代二次元文化不同,《夏目友人帐》所独有的特质是为当下的日本保留了一份“前现代”的空间。故事诞生、发展的场域被牢牢地限定在相对不发达的九州岛上,也正因为这份不现代乃至落后的味道,《友人帐》的故事得以成立。不同于《名侦探柯南》,侦探以及他所关注的案件,包括展现探案过程的侦探小说,都是极其现代的存在,柯南可以出现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不管是“民风淳朴”的米花町,还是金田一式下乡怪谭,观众读者都可以欣然接受,但是《友人帐》不行,它的“落后”犹如猫咪老师慵懒的语调,只有在那里才可以。
发展内山节的观点,狐狸(以及其他的动物)作为神明在世间的“式神”(一种化身),是日本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稳定期,一种中介,一种解读世界的方式。
以《夏目友人帐》为例,每个故事都是以发现灵异现象作为开始,现象下的本质都是有妖怪在捣乱,普通人只是把这些怪异的情况当作偶然,只有看得见妖怪的主人公会去探寻妖怪作乱的缘由,由此生发追忆,产生一种现代人需求的温情与疗愈。我们假设这样与鬼怪相遇的故事发生在东京、大阪这样的现代都市,那么如此慢的节奏与现代都市的穷追猛打就会产生巨大的割裂,怕不是要改成捉鬼、杀妖才能合乎受众的胃口,我们只有在九州的农村才能接受夏目和猫咪老师为我们提供的温情一刻。
内山节在书里说,1965年之后,日本就不再被狐狸所欺骗了,这其实是“乡土日本”这一概念的彻底瓦解。熟悉日本近代史的读者或许会有疑问,通常我们把发轫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一历史节点作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缘何要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日本人才不相信狐狸?我们或许可以参看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坂上之云》。这个故事讲述了从四国高松走出的几位明治风云人物,以极为个人的视角为公众展现了彼时日本的风貌。在后续制作的电视剧集的开头,旁白是这样表述的,在那个列强纷争的时代里,没有比日本更小的国家了,这个国家基本完全依赖农业,识字率极低,却想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获得可以和列强抗衡的军事力量,想要跻身列强之流,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司马辽太郎没有抛却的是“二战”前日本从近代向现代前进过程中那“沉重的肉身”,武士道、儒教、神道教所代表的传统依旧支配着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方兴未艾,乡村依旧是日本的大部分,也是支撑日本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然而“二战”的彻底失败,从根本上击溃了“乡土日本”的残存力量,动摇了狐狸们所支配的空间与场域,日本人认识到,“神风”精神,以及发轫于“武士道”扭曲为效忠军国主义的“一亿玉碎”,这些精神力在美国强大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能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创伤直接刺激着战后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促使民众用迷信、谎言来定义狐狸和它的朋友们。在这种矫枉过正的思潮下,学习理工科,被认为是更好的出路,至于“人为什么而活”这种不会产生经济效益的问题,与狐狸们一道被扔在了无人关心的角落。“乡土日本”的瓦解——传统的仪式、祭奠、手艺,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一并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那种需要“年幼者从年长者那里获得的东西”被束之高阁。乡村共同体消散,取而代之以现代、文明的原子化家庭。信息传播的载体与“经济”“科学”一道促生了故事的重大转变,口口相传的添油加醋让位于广播、电视、报纸相对严谨、公允的“报道”,一种“客观”的幻觉取代了蒙昧。人们接受信息的步骤被缩减,信息不再需要“读取”,更多的是被输入、灌输。
自然的价值不再停留在感觉层面,如果不能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自然就是无用的。但是这种复杂的感觉,并不能在狂热的经济时代下带来直接的收益,新的图景被战后政府放置在国民眼前,惊涛骇浪般的城市化,飞速进入小家庭肢解原先劳动感的各种高科技家电,西方舶来的各种物质序列、娱乐方式。解读狐狸、编纂狐狸的理由变得不再充分,也不再必要。虽然战后的日本面临着诸多分岔路口的选项,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经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神明”,它从头到脚支配了日本,统摄着那个时代。
实际上,不论群马县深山里的内山节如何呼喊,狐狸以及它所活跃的“乡土日本”注定是需要被符号化、奇观化的。日本的公众或许愿意支付不菲的价格,花不少时间,前往山中进行民俗体验,又或者是加入“摇曳露营”的风潮,开着自驾车满载一堆现代的露营设备前去体验自然。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以及它所改变的人类感觉结构是不可逆的。作者清晰地写到,被刻意忽略的“日本村落史”也是日本过去(历史)的一部分,它甚至可以作为反思进步(线性)史观的基点。用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评价过去,很容易为过去打上一个“落后”的标签,因为我们是现在的我们,这种无意识“恶意”的改写,塑造了历史的面貌。那些不符合当下价值标准的事物被隐藏。在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关系中展开的历史,在当下价值标准中会变成“看不见的历史”;在生者与死者互相关联的状态中展开的历史也是一样。——人被狐狸欺骗的历史也会被简化为“前人的可笑故事”,在读完《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欺骗了?》之后,内山节的身边似乎多了几张故人的脸庞——竹内好、沟口雄三……当然还有活着的村上春树。

“一面眼看着山坡上人家错落的灯火,一面脚底慢慢往下走。有黑暗的森林、小小的山丘,有几处地方白色水银灯照出私家游泳池的水面反光。坡面的斜度终于减弱下来的地方,有一条跟地表结合在一起的光带似的高速公路蛇行着,越过那里一直到海的一公里左右,则被平板的街容占据着。然后是黑暗的海,海和天的暗影区分不明地融合起来。在那黑暗之中,灯塔的橘红色光,浮现,又消失。而一条幽暗的水路笔直地贯穿其间,将这些清晰的断层切开。那是河。”在《听风的歌》这部处女作里,村上不乏这种看似无用的闲笔,这恰恰是一种接续了夏目漱石的味道——对日本现代化的质疑。犹如狐狸文化诞自中国一般,日本的现代图景也是“借来”的,是仓岩使节团带回来的,是麦克阿瑟指导出来的,森林和高速公路的图景,犹如日本暧昧不明的自主性,狐狸遁走山林,带来的是无尽的怅惘,它可以具化为村上春树驰名海内的标签——“无感”,亦是高悬在现代日本之上的无尽迷思。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