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被称之为“东西”,源自何时?有个玄妙的说法,“民生日用所需俱出于木,而以金易之”,古人日常使用的物件大多木制,且要花钱来买,木属东,金属西,因此,物件就被称为“东西”。
东西这个词,用在人身上,就有轻蔑羞辱的意思。问别人的来历时,就算预先脱帽鞠躬,也不能问他是什么东西。这话一出口,前面的种种努力就像挑衅,很容易打起来。但中文的精妙在于,你也不能说对方“不是东西”。这话出口,一样打架。
但回到自己,倒是可以自称“东西”的。
家父刚过70岁时,我带他去敦煌旅行。当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并不真的理解人体机能会随着年龄增长急转直下。在兰州,我买了卧铺火车票,本意是想和老父亲一路西行,饱看西北苍茫美景。
一日一夜的火车到站后,我只觉得自己是个被抽干了水分的仙人掌。再看老父亲,累得眉眼都耷拉着,显是筋疲力尽。出站就近找了个酒店,在大而松软的床上又饱睡了一觉。等我醒来,睁眼一看,暮色将近。窗前,父亲坐着,捧着伴随他多年的保温杯,悠悠地喝着茶。我问他睡了多久?他说老东西了,睡不久,哪像你,沾枕头就打呼噜,打雷都不醒。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自称老东西,语气里带点调侃,更多的是无奈和沧桑。
两年后,我和他还去过一次台湾。在台北西门町逛了会,我便要带他去一家有名的鸭血豆腐火锅店吃午饭。步行到店,路程不到两公里。台北路窄,小巷也多,跟着导航,一路穿街过巷,正好可以看看台北风情。
小时候,父亲最爱带着我在上海街头步行,接近于现在的Citywalk,一走就是三公里以上。他走得快,我得迈开小短腿,在他后面紧紧跟着,背着个小书包,真像急行军。
我早已习惯和他一起“暴走”了,但没想到,这次路程不过一半,老父亲就要坐下来歇,还着急找洗手间。上了厕所歇了会儿,再走。他慢,我老在他前头等着,好不容易到了店,正碰上人最多的时候,只好坐在门口等位。趁着这时候,老父亲又去了次厕所,回来颤巍巍坐下,摇摇头说,老东西,真走不动了。
老人糖尿病尿频,所以老要上厕所。后来,我咨询了医生,才懂。
那是我第二次听他自称老东西,语气里没有了调侃,全是无奈。
今年年初,父亲走了。走得突然,没有预兆。邻居后来说,走的那天早上,还看到他在小区里乐呵呵地遛弯。但人生无常,一转身就是永别。当晚他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我第二天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冷。
作家陈丹青说,死亡是一条老狗,又残忍又无意义。我同意他的话。父亲不再是“老东西”,而真成为了一件没活气儿的东西,这一幕让我觉得人生确乎残忍且无意义。
他走后,我花了两个多月收拾家里。一百三十二平米的房子,足够放下很多很多东西。我一人一猫,在房里翻来翻去,像在时间的河流里寻宝。我翻到了十几年前的衣服,二十几年前的老照片,还有用了三四十年的羊毛毯,最久远的是太奶奶传给父亲的一枚金戒指,按老法理应传给我的媳妇、我儿媳妇。
我没媳妇,更没有儿媳妇,大概率也不会再有了。他和我、还有他和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一切终将默默湮灭,就像从没来过这个世界。可惜了,“老东西”的好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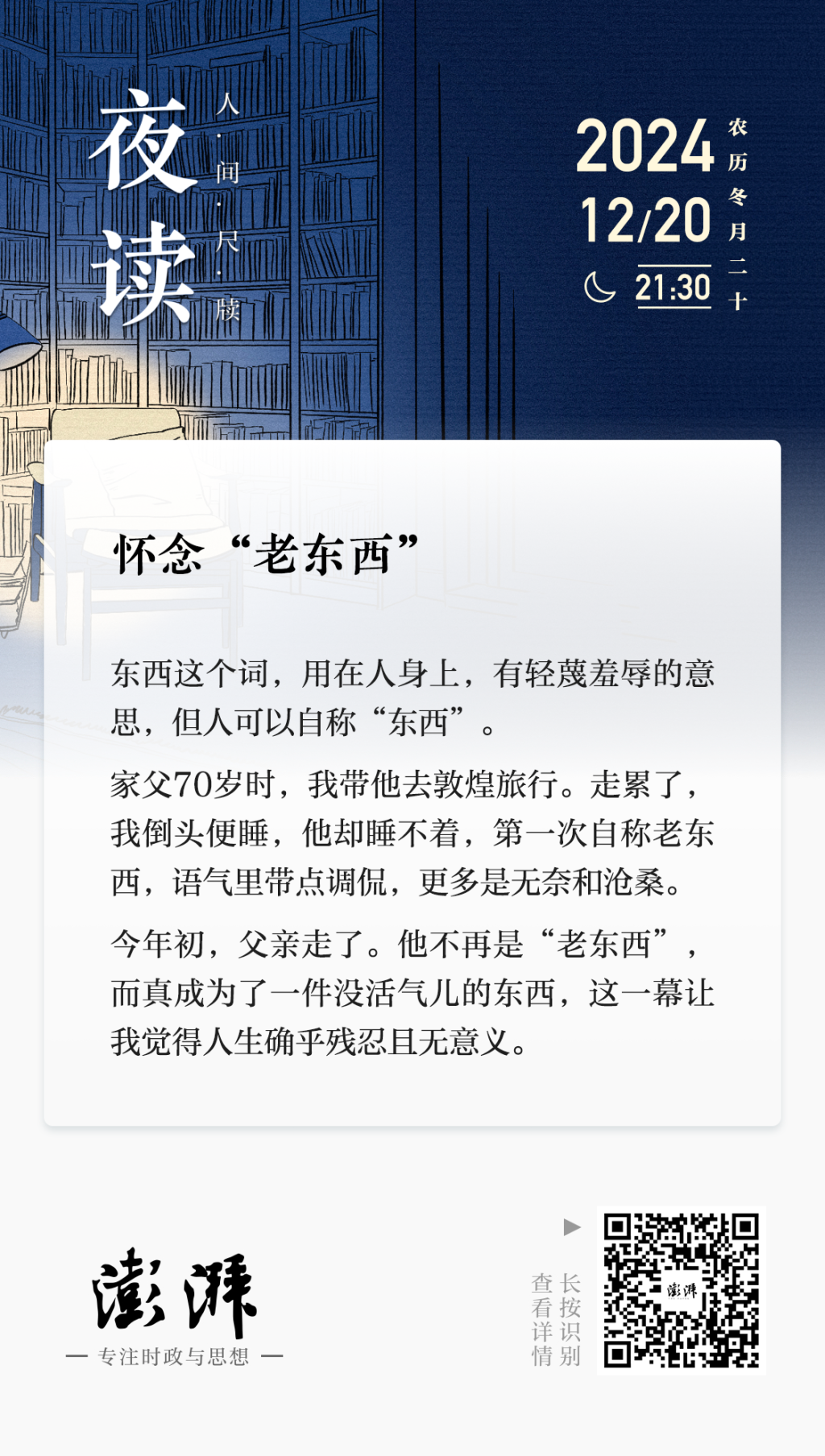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